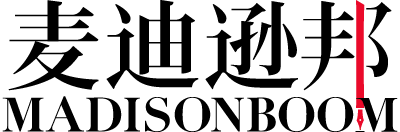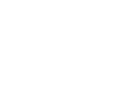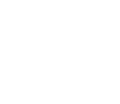人生充满矛盾。你做得比较好的事情,你却很讨厌做。我就曾经在这个矛盾漩涡里打转。
70年代中,至80年代后期,那十多个年头我也在广告公司混饭吃。开始的时候,我也曾热爱广告创作,但搞搞,所牵涉的华洋之争、虚伪、作大、多余、扮、呃客户钱(很简单,把每样大小「广告费用」例如制作费,也谷大)、舔客户屁股,这些一切与创作无关的事情,实在令我倒胃。
广告创作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难度。反而交际应酬,插科打诨,与客户friend,与洋同事(多数是你的上司)保持良好关系,这些一般人轻易做到的事,我怎努力也做不到。
也许是自己贪图安逸(唔通去担去抬咩?),也许没有勇气冲出这个讨厌却又易搵食的圈子,便滞留其内,差点滞死。
当中,固然有些好日子,也有不少野蛮的日子……
变身之前
当上不结领带的广告人之前,我天天结领带穿西装返工。
阿妈很高兴,她认为打呔着西装上班的工,都是不错的好工。
那时我廿多岁,在某美资银行新成立的计算机部门里面,当一个初级系统分析员(systems analyst),月薪二千五。我对这份工作很有兴趣,很投入,和同事上司们很合得来。
也学到很多东西。部门主管阿Dave,一个四十多岁的美国佬,经验非常丰富,干劲十足,没有架子,乐于指导后进,也放手让你去做。Dave虽然专业,其为人和样子却诙谐。他走路步伐很快,头顶是个地中海,但余下的头发鬈曲得很,要是他突然止步,你会看见他的身体静止了,但那些弹弓般的曲发,仍会在头上弹弹,煞不住掣似的。
其他比我有更多经验的本地同事,都很年轻,他们也很乐意把所懂的,说给我知。不知道是那个年代的人较易相处,还是那个年代的人比较随和,总之,至今,这份工仍带给我不少好回忆。
有一次,我们要向银行一个荷兰鬼佬高级副总裁,做一个presentation。主管Dave和我们「彩排」了很多次,一切就绪。
那个洋副总裁,是银行中人所皆知的醉猫,每到下午就已饮得面红红,绰号「油炸蟹」,且脾气大,众人都怕他。
我们正式做presentation的那个下午,太阳火红,「油炸蟹」的脸更红。
轮到我那一part,我说不了三四句,刚举起第一个图表,「油炸蟹」便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霍然起身离场。我们登时「哑」。
我记得,我在洗手间落泪。没试过这样难受。这是我的第一次presentaion。
主管Dave很愤怒。单独和我谈了一阵子,并说一定要「油炸蟹」向我道歉。我说算了算了,Dave说这些事情不可以就此就算。过了约一星期,「油炸蟹」突然召见我。他的办公室在尊贵的中环(我们的在湾仔分域街,酒吧附近)。
这是我首次来到「总部」。在层数很高的「油炸蟹」office内,「油炸蟹」的脸今天未算太红,可能是上午,还未有机会喝太多酒。他我坐下,说,你就是Richard Lam?你们的project进行得顺利吗?哦,哦,好,有机会再谈。
上星期中途离场的事,他提也不提,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道歉。但我也算了,那时我还未开始变野蛮。
后来,不知是因为什么政治问题,主管Dave被高层逼走,换来一个不知所谓的美国佬。这条友是个外行,对我们所做的一切,完全不了解,但又要扮识,阿芝阿佐。我和这盲炳无法沟通,谷住条气,终于劈炮。
第一站——靠熟人
离开了我的系统分析生涯,脱下了我的西装领呔(我阿妈担心我从此踏入歧途),不知何故,我忽然强烈觉得:我要做个广告创作人,把那行业改写!
每看见或听见广告,心中就有堆烈火,那烈火还会说话:挑,咁老土,等我啦!
于是我写信向广告公司求职。我全无经验,全无往绩,当然没有人回信。人家总不能因为你自己心中有把声音在说「挑,咁老土,等我啦」,就认为你有料到。
绝望之际,忽然有一间全华资的广告公司约见。那时全华资的广告公司甚少,多数都是外资的。Interview我的,是该公司的太子爷。他的行为举止,很戏剧化,忽然从大班椅中一跃而起,跃到我面前,问我,五年后,想不想坐上这张椅。我说当然想。
之后,这公司再没有人和我联络了。是不是因为有关大班椅的那条问题,我的答案严重出错?我听见我心中那把烈火在说:挑,间公司咁老土,请我都唔去!
姊姊和黄沾,当时正在筹备创办「黄与林广告」。我既然无法混得进当时我认为要由我来改写的广告行业(尽管我一个广告也没做过出来),便唯有靠熟人入行。幸而「黄与林广告」肯收留我。[编者按:林振强的姐姐就是香港女作家林燕妮]
初开档的「黄与林」,其实都几好笑。真正有广告宣传经验的人,就只得两个。黄沾和我姊(她之前是TVB的宣传部主管)。
水禾田是我们的美术总监。阿水虽是著名摄影家,但他不是广告人。其他人包括我,全是新丁。于是我们一伙人盲冲乱撞,都也甚好玩。而黄林二人,也争取到一些很不俗的客户。
黄沾是当时广告界的顶尖创作人,我从他身上学了些皮毛,已很受用。他也放手让我胡来,我很感激。后来,业界猛人Joe Wang,从李奥贝纳(Leo Burnett)跳槽过来,把discipline和「专业」注入这乱作一团的小公司,「黄与林」才得以逐渐变得professional起来。
我在这儿工作了约年半,很愉快。但,我觉得是时候离开熟人,出外面闯,和陌生人交手了。黄林二人也了解我这种心情。
走进外面的森林之后,渐渐,不知不觉,我变得暴戾,和野蛮……
初跳草裙
多得童年好友「牛仔」穿针引线,我转投到McCann-Ericsson。
在那处,我有机会为一些顶级的国际品牌做广告,渐渐也做到一些成绩出来。后来,机缘巧合,因为做广告歌,在录音室被唱片公司某要员看中,给我参与填词的机会。
(我的「填词人」身份,对于后来我与鬼佬们的角力和斗争,扮演了一个颇有用的角色。)
好友牛仔,当时是M记的高层(现在是主板上市公司主席),不单止是一流广告人,还是处理办公室政治的一等一高手。当时的创作总监,是美国人Stoney Mudd,人不错,但久不久总要找一些事情出来,和牛仔作政治斗争,有时还牵涉到我的创作。幸而牛仔每每把那些斗争一一挡开,让我不受影响,专心做我的创作。
在M记工作了大半年,我有幸做了几个口碑和推销力都不错的广告,而另一方面,我的填词工作也开始有少许成绩。
那时刚踏入八十年代,我的月薪大约四千多块,有老婆,但没有钱置业。我自己暗中定下目标:要在短期之内,月薪一万元。这目标对我来说,遥不可及。
正不知从何入手那一万元,机会却送上门。Leo Burnett(李奥贝纳)的创作总监,人称毕叔的英国人Richard Butt来挖角。我和他吃午饭会面谈条件。我硬头皮,斗胆要求月薪一万,都算狂妄野蛮。毕叔竟然说没有问题。我答应下个月上班。
回到M记,我开始跳草裙舞,和Stoney谈判,并透露某某以一万元挖我,你打算怎做。结果M记出同样价钱留我。
在M记,我和牛仔合作得很好,也有很多机会发挥,我很感谢他「照住」我。既然那「一万大元目标」已达,我决定在M记多留一回。
当我打电话告知毕叔我改变主意,不加盟了。他说如果这样做,你认为对得住良心,就这样做吧。
挑!别跟我讲耶稣,别跟我讲良心,我要的是一万块钱!
阿袋
继续在M记工作,跟Stoney相处得也没怎样,但我知道不能久留。跳过一次草裙舞的人,公司是不会信任的。
然后有一天,素未谋面的John Doig打电话给我。
John Doig,人称「阿袋」,纽西兰人。他是当时最负盛名、最富争议性、最自负的创作总监,也是最有料到的创作鬼佬。(传说:John Doig咄咄逼人的爆棚信心,曾窒到另一位他看不起的鬼佬创作总监,以后说话也口吃。)
John说,我的一位旧同事Louis Ng向他推荐我。(Louis Ng吴峰豪,为人低调,是我最敬重的人之一,后来成为首屈一指的广告片导演,佳作如云,获国际大奖无数。)他想我加入他们新成立的Ogilvy & Mather(奥美)分店Meridian。
终于面对面和John Doig谈条件。「阿袋」是个大胡子,三十多岁,一双蓝眼睛非常精灵,和咸湿。谈薪酬,非常畅顺,比我预期的高。谈到职衔,却差点僵住。我记得我们当时的对话,大概是这样的,我开始野蛮:
袋(刻意地漫不经意):职衔并不重要。
我:对我来说很重要。
袋:那么你的title就是Chinese Creative Director吧。
我:为什么要有Chinese这个字?你又为什么不叫做English Creative Director?
(一时之间,dead air)
我:我不要有Chinese这个字。
袋(问在旁的鬼佬执行董事):如何?
执行董事(略一沉吟):好吧,那就叫做Creative Director吧。
其实,我暗里一额汗。我从未试过这样大胆,和横蛮,可能因为实在无法再忍受不公平待遇。我要学会保护自己,由职衔开始。
以尿浇花
其实和阿袋合作,是一件愉快的事。他自信心爆棚,所以绝不会搞小动作整蛊你。反而,他会尽力协助我把广告制作得很好。他除了是个精彩的创作人,还是一个很出色的制作人,虽然有时他饮多了几杯,午饭后会在公司的露台屙尿淋花。
这个期间(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填词方面闯出了点名堂。我尽量保高调,接受所有访问和曝光机会。人家访问我,我就约他们上来公司,好让那些鬼佬知道我并不是个二打六,别对我阿芝阿佐。这方法好像有点效用。同时,在客户眼中,因为我有点名气,他们对我也多了点信心,办起事上来,有时(只是有阵时)有点方便。
不过,在Meridian的期间,有些华人客户仍然教我作呕。他们来开会,往往一定要我们有鬼佬出席,对我们华籍创作人不放心。有时,他们被阿袋不客气地窒到飞起,却又不敢出声,事后却诸多投诉,好核突。
本来,一切尚算相安无事,直至阿袋自己跳草裙舞。他认为香港不够专业,要往美国发展。(按:阿袋后来果然在美国广告界打出名堂,《时代》周刊也报道过。)阿袋扰扰攘攘之际,公司又从外地进口了几个不知来港做什么的鬼佬。我三番四次被「逼迁」——我的「名气」暂时「失灵」——办公室越搬越小,小得像鞋盒,非常无瘾。加上阿袋就快离开,我将没有良师,于是也兴起劈炮之心。
殴打客户
也许这是我的运气,每次想转工,也恰好遇上有公司搵人。
我跳槽到Kenyon & Eckhardt,阿袋说我黐线。这公司的前身,有个鬼佬创作总监,就是被阿袋窒到飞起、后来变了口吃的那位仁兄,所以阿袋老是瞧不起这公司。
K记当时全面大革新,招兵买马。新fit人,是以前在「黄与林」合作过的Joe Wang。再度合作,我们完全没有问题。此外,昔日在McCann-Ericsson的旧拍档,美术总监「阿财」,不久也加盟了。和合作惯的人共事,事半功倍。
可是,当时的K记,客户实在不算多,我们需要不停生意,不停做presentation,颇辛苦。手上仅有的两三个大客户,又要服侍周到,有时的确有点吃不消。
我记得我们有一个都算重要的客户,是一间华资公司。无论我们做了些什么创作,他们永远不满,永远要弹!弹!弹!要改!改!改!
有一回,千辛万苦,广告片剧本修改了九百七十三次之后,终于把广告片拍了出来,但他们不满意。于是又再补拍,再做过某些动画,某些特别效果,等等,但他们仍是不满。
我终于忍不住,有次在放映室中,走近那客户代表,和他差不多面贴面,以低沉兼带有恐吓性的声调问他:「你究竟想点?!」幸而他没有话说,不然可能以只揪收场。
要鬼有鬼
在K记改革的初期,我们并没有鬼佬创作总监(其实亦无需要),一切自己搞掂。Joe Wang的英文一流,并颇有创作天分。要是他不做Managing Director,他可以是个出色的创作人。
总之,少一只鬼,少十万样烦事。
可惜,那些国际品牌的大客户,不见鬼不欢。结果,我们的美国总公司,不知从哪儿调派了一只鬼佬创作总监过来。当然,此君的薪金比我高,办公室比我的大。
不过,最好笑的,不是我们有偏见,而是,这条友真的很渣,根本不会做广告创作。(后来才发现,这人原来是写——或希望写——电影剧本的。至于他有没有作品被拍成电影,没有人知道。)Joe Wang唯有把他投闲置散,有客户要见鬼时,便拿他出来让他们见见。回想起来,实在像幕荒诞剧。难得的是,此君也够厚面皮,天天大剌剌的坐在办公室内无所事事,白高薪。
棺材精公司只得一只鬼,麻烦事算不多了。然而,不知是不是那个年代,还是现在也是一样,你的公司没有多几只鬼佬,就很难抢到也是鬼佬fit的大客户。
不知是总公司的安排,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终于,另一间本地的外资广告公司的鬼佬头头,带领他的亲信——又是鬼佬一名——「入侵」我们这间K记。
那个「亲信」,我依稀记得名叫Michael Holt,美国人,貌似棺材精。他其实是个监制(producer),却不知怎地变身成为了创作总监,还带了个华籍的美术总监过档。
我和这个棺材精,不知何解,无法相处。不知是他样衰还是态度问题,总之见到他我就无明火起。我们的「合作程度」,从以下的对话可现一斑:
棺:Richard,你可以为我把这段英文译为中文吗?
我:当然可以,如果你可以为我把这段中文译为英文。
棺:但我不懂中文。
我:那是你的问题。
厌倦森林
天天这样「斗争」,和「不合作」,我开始感到疲倦。
脾气越来越差,烟抽得越来越多。要不是我还可以以填词来平衡一下,我恐怕我早已疯了。我那首想回到平淡、不再指桑骂槐、不想追名逐利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好像也是在这期间写的。
每天,我都不想上班。即使回到公司,也是扳着脸。我还先后把两位女同事弄哭了,因为我不肯修改稿件,也不肯和客户开会,教她们无法向客户交代。她俩本来都是跟我谈得来的好同事。
许多时候,我在公司附近的茶餐厅吃早餐,吃至十一时许仍不离开。一边狂抽烟,一边填词,我根本不想见到公司那些鬼。拍档阿财,有时要走来找我,并「劝」我返工。
不过,即使返回公司,午膳时我又会吃到三四点,才再会在公司露面。
我实在很倦很倦,我不能继续这样过日子。我很想,很想离开这个广告界森林。
后记
后来发生的事情,有点复杂。
总之,机缘巧合,一九八八年,我脱离了广告界,加入了黎智英的集团。他改变了我的下半生。
最精彩的一句
苹果计算机创办人之一Steve Jobs,还是个廿来岁的嬉皮士时,欲邀请当时百事可乐的总裁(四十多岁)加盟,便对他说:「你打算下半世继续卖糖水(sugared water),还是你想改变世界?」
我不想下半生也卖糖水。
林振强
原刊于《壹周刊》
转自:Facebook
人生充满矛盾。你做得比较好的事情,你却很讨厌做。我就曾经在这个矛盾漩涡里打转。
70年代中,至80年代后期,那十多个年头我也在广告公司混饭吃。开始的时候,我也曾热爱广告创作,但搞搞,所牵涉的华洋之争、虚伪、作大、多余、扮、呃客户钱(很简单,把每样大小「广告费用」例如制作费,也谷大)、舔客户屁股,这些一切与创作无关的事情,实在令我倒胃。
广告创作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难度。反而交际应酬,插科打诨,与客户friend,与洋同事(多数是你的上司)保持良好关系,这些一般人轻易做到的事,我怎努力也做不到。
也许是自己贪图安逸(唔通去担去抬咩?),也许没有勇气冲出这个讨厌却又易搵食的圈子,便滞留其内,差点滞死。
当中,固然有些好日子,也有不少野蛮的日子……
变身之前
当上不结领带的广告人之前,我天天结领带穿西装返工。
阿妈很高兴,她认为打呔着西装上班的工,都是不错的好工。
那时我廿多岁,在某美资银行新成立的计算机部门里面,当一个初级系统分析员(systems analyst),月薪二千五。我对这份工作很有兴趣,很投入,和同事上司们很合得来。
也学到很多东西。部门主管阿Dave,一个四十多岁的美国佬,经验非常丰富,干劲十足,没有架子,乐于指导后进,也放手让你去做。Dave虽然专业,其为人和样子却诙谐。他走路步伐很快,头顶是个地中海,但余下的头发鬈曲得很,要是他突然止步,你会看见他的身体静止了,但那些弹弓般的曲发,仍会在头上弹弹,煞不住掣似的。
其他比我有更多经验的本地同事,都很年轻,他们也很乐意把所懂的,说给我知。不知道是那个年代的人较易相处,还是那个年代的人比较随和,总之,至今,这份工仍带给我不少好回忆。
有一次,我们要向银行一个荷兰鬼佬高级副总裁,做一个presentation。主管Dave和我们「彩排」了很多次,一切就绪。
那个洋副总裁,是银行中人所皆知的醉猫,每到下午就已饮得面红红,绰号「油炸蟹」,且脾气大,众人都怕他。
我们正式做presentation的那个下午,太阳火红,「油炸蟹」的脸更红。
轮到我那一part,我说不了三四句,刚举起第一个图表,「油炸蟹」便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霍然起身离场。我们登时「哑」。
我记得,我在洗手间落泪。没试过这样难受。这是我的第一次presentaion。
主管Dave很愤怒。单独和我谈了一阵子,并说一定要「油炸蟹」向我道歉。我说算了算了,Dave说这些事情不可以就此就算。过了约一星期,「油炸蟹」突然召见我。他的办公室在尊贵的中环(我们的在湾仔分域街,酒吧附近)。
这是我首次来到「总部」。在层数很高的「油炸蟹」office内,「油炸蟹」的脸今天未算太红,可能是上午,还未有机会喝太多酒。他我坐下,说,你就是Richard Lam?你们的project进行得顺利吗?哦,哦,好,有机会再谈。
上星期中途离场的事,他提也不提,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道歉。但我也算了,那时我还未开始变野蛮。
后来,不知是因为什么政治问题,主管Dave被高层逼走,换来一个不知所谓的美国佬。这条友是个外行,对我们所做的一切,完全不了解,但又要扮识,阿芝阿佐。我和这盲炳无法沟通,谷住条气,终于劈炮。
第一站——靠熟人
离开了我的系统分析生涯,脱下了我的西装领呔(我阿妈担心我从此踏入歧途),不知何故,我忽然强烈觉得:我要做个广告创作人,把那行业改写!
每看见或听见广告,心中就有堆烈火,那烈火还会说话:挑,咁老土,等我啦!
于是我写信向广告公司求职。我全无经验,全无往绩,当然没有人回信。人家总不能因为你自己心中有把声音在说「挑,咁老土,等我啦」,就认为你有料到。
绝望之际,忽然有一间全华资的广告公司约见。那时全华资的广告公司甚少,多数都是外资的。Interview我的,是该公司的太子爷。他的行为举止,很戏剧化,忽然从大班椅中一跃而起,跃到我面前,问我,五年后,想不想坐上这张椅。我说当然想。
之后,这公司再没有人和我联络了。是不是因为有关大班椅的那条问题,我的答案严重出错?我听见我心中那把烈火在说:挑,间公司咁老土,请我都唔去!
姊姊和黄沾,当时正在筹备创办「黄与林广告」。我既然无法混得进当时我认为要由我来改写的广告行业(尽管我一个广告也没做过出来),便唯有靠熟人入行。幸而「黄与林广告」肯收留我。[编者按:林振强的姐姐就是香港女作家林燕妮]
初开档的「黄与林」,其实都几好笑。真正有广告宣传经验的人,就只得两个。黄沾和我姊(她之前是TVB的宣传部主管)。
水禾田是我们的美术总监。阿水虽是著名摄影家,但他不是广告人。其他人包括我,全是新丁。于是我们一伙人盲冲乱撞,都也甚好玩。而黄林二人,也争取到一些很不俗的客户。
黄沾是当时广告界的顶尖创作人,我从他身上学了些皮毛,已很受用。他也放手让我胡来,我很感激。后来,业界猛人Joe Wang,从李奥贝纳(Leo Burnett)跳槽过来,把discipline和「专业」注入这乱作一团的小公司,「黄与林」才得以逐渐变得professional起来。
我在这儿工作了约年半,很愉快。但,我觉得是时候离开熟人,出外面闯,和陌生人交手了。黄林二人也了解我这种心情。
走进外面的森林之后,渐渐,不知不觉,我变得暴戾,和野蛮……
初跳草裙
多得童年好友「牛仔」穿针引线,我转投到McCann-Ericsson。
在那处,我有机会为一些顶级的国际品牌做广告,渐渐也做到一些成绩出来。后来,机缘巧合,因为做广告歌,在录音室被唱片公司某要员看中,给我参与填词的机会。
(我的「填词人」身份,对于后来我与鬼佬们的角力和斗争,扮演了一个颇有用的角色。)
好友牛仔,当时是M记的高层(现在是主板上市公司主席),不单止是一流广告人,还是处理办公室政治的一等一高手。当时的创作总监,是美国人Stoney Mudd,人不错,但久不久总要找一些事情出来,和牛仔作政治斗争,有时还牵涉到我的创作。幸而牛仔每每把那些斗争一一挡开,让我不受影响,专心做我的创作。
在M记工作了大半年,我有幸做了几个口碑和推销力都不错的广告,而另一方面,我的填词工作也开始有少许成绩。
那时刚踏入八十年代,我的月薪大约四千多块,有老婆,但没有钱置业。我自己暗中定下目标:要在短期之内,月薪一万元。这目标对我来说,遥不可及。
正不知从何入手那一万元,机会却送上门。Leo Burnett(李奥贝纳)的创作总监,人称毕叔的英国人Richard Butt来挖角。我和他吃午饭会面谈条件。我硬头皮,斗胆要求月薪一万,都算狂妄野蛮。毕叔竟然说没有问题。我答应下个月上班。
回到M记,我开始跳草裙舞,和Stoney谈判,并透露某某以一万元挖我,你打算怎做。结果M记出同样价钱留我。
在M记,我和牛仔合作得很好,也有很多机会发挥,我很感谢他「照住」我。既然那「一万大元目标」已达,我决定在M记多留一回。
当我打电话告知毕叔我改变主意,不加盟了。他说如果这样做,你认为对得住良心,就这样做吧。
挑!别跟我讲耶稣,别跟我讲良心,我要的是一万块钱!
阿袋
继续在M记工作,跟Stoney相处得也没怎样,但我知道不能久留。跳过一次草裙舞的人,公司是不会信任的。
然后有一天,素未谋面的John Doig打电话给我。
John Doig,人称「阿袋」,纽西兰人。他是当时最负盛名、最富争议性、最自负的创作总监,也是最有料到的创作鬼佬。(传说:John Doig咄咄逼人的爆棚信心,曾窒到另一位他看不起的鬼佬创作总监,以后说话也口吃。)
John说,我的一位旧同事Louis Ng向他推荐我。(Louis Ng吴峰豪,为人低调,是我最敬重的人之一,后来成为首屈一指的广告片导演,佳作如云,获国际大奖无数。)他想我加入他们新成立的Ogilvy & Mather(奥美)分店Meridian。
终于面对面和John Doig谈条件。「阿袋」是个大胡子,三十多岁,一双蓝眼睛非常精灵,和咸湿。谈薪酬,非常畅顺,比我预期的高。谈到职衔,却差点僵住。我记得我们当时的对话,大概是这样的,我开始野蛮:
袋(刻意地漫不经意):职衔并不重要。
我:对我来说很重要。
袋:那么你的title就是Chinese Creative Director吧。
我:为什么要有Chinese这个字?你又为什么不叫做English Creative Director?
(一时之间,dead air)
我:我不要有Chinese这个字。
袋(问在旁的鬼佬执行董事):如何?
执行董事(略一沉吟):好吧,那就叫做Creative Director吧。
其实,我暗里一额汗。我从未试过这样大胆,和横蛮,可能因为实在无法再忍受不公平待遇。我要学会保护自己,由职衔开始。
以尿浇花
其实和阿袋合作,是一件愉快的事。他自信心爆棚,所以绝不会搞小动作整蛊你。反而,他会尽力协助我把广告制作得很好。他除了是个精彩的创作人,还是一个很出色的制作人,虽然有时他饮多了几杯,午饭后会在公司的露台屙尿淋花。
这个期间(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填词方面闯出了点名堂。我尽量保高调,接受所有访问和曝光机会。人家访问我,我就约他们上来公司,好让那些鬼佬知道我并不是个二打六,别对我阿芝阿佐。这方法好像有点效用。同时,在客户眼中,因为我有点名气,他们对我也多了点信心,办起事上来,有时(只是有阵时)有点方便。
不过,在Meridian的期间,有些华人客户仍然教我作呕。他们来开会,往往一定要我们有鬼佬出席,对我们华籍创作人不放心。有时,他们被阿袋不客气地窒到飞起,却又不敢出声,事后却诸多投诉,好核突。
本来,一切尚算相安无事,直至阿袋自己跳草裙舞。他认为香港不够专业,要往美国发展。(按:阿袋后来果然在美国广告界打出名堂,《时代》周刊也报道过。)阿袋扰扰攘攘之际,公司又从外地进口了几个不知来港做什么的鬼佬。我三番四次被「逼迁」——我的「名气」暂时「失灵」——办公室越搬越小,小得像鞋盒,非常无瘾。加上阿袋就快离开,我将没有良师,于是也兴起劈炮之心。
殴打客户
也许这是我的运气,每次想转工,也恰好遇上有公司搵人。
我跳槽到Kenyon & Eckhardt,阿袋说我黐线。这公司的前身,有个鬼佬创作总监,就是被阿袋窒到飞起、后来变了口吃的那位仁兄,所以阿袋老是瞧不起这公司。
K记当时全面大革新,招兵买马。新fit人,是以前在「黄与林」合作过的Joe Wang。再度合作,我们完全没有问题。此外,昔日在McCann-Ericsson的旧拍档,美术总监「阿财」,不久也加盟了。和合作惯的人共事,事半功倍。
可是,当时的K记,客户实在不算多,我们需要不停生意,不停做presentation,颇辛苦。手上仅有的两三个大客户,又要服侍周到,有时的确有点吃不消。
我记得我们有一个都算重要的客户,是一间华资公司。无论我们做了些什么创作,他们永远不满,永远要弹!弹!弹!要改!改!改!
有一回,千辛万苦,广告片剧本修改了九百七十三次之后,终于把广告片拍了出来,但他们不满意。于是又再补拍,再做过某些动画,某些特别效果,等等,但他们仍是不满。
我终于忍不住,有次在放映室中,走近那客户代表,和他差不多面贴面,以低沉兼带有恐吓性的声调问他:「你究竟想点?!」幸而他没有话说,不然可能以只揪收场。
要鬼有鬼
在K记改革的初期,我们并没有鬼佬创作总监(其实亦无需要),一切自己搞掂。Joe Wang的英文一流,并颇有创作天分。要是他不做Managing Director,他可以是个出色的创作人。
总之,少一只鬼,少十万样烦事。
可惜,那些国际品牌的大客户,不见鬼不欢。结果,我们的美国总公司,不知从哪儿调派了一只鬼佬创作总监过来。当然,此君的薪金比我高,办公室比我的大。
不过,最好笑的,不是我们有偏见,而是,这条友真的很渣,根本不会做广告创作。(后来才发现,这人原来是写——或希望写——电影剧本的。至于他有没有作品被拍成电影,没有人知道。)Joe Wang唯有把他投闲置散,有客户要见鬼时,便拿他出来让他们见见。回想起来,实在像幕荒诞剧。难得的是,此君也够厚面皮,天天大剌剌的坐在办公室内无所事事,白高薪。
棺材精公司只得一只鬼,麻烦事算不多了。然而,不知是不是那个年代,还是现在也是一样,你的公司没有多几只鬼佬,就很难抢到也是鬼佬fit的大客户。
不知是总公司的安排,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终于,另一间本地的外资广告公司的鬼佬头头,带领他的亲信——又是鬼佬一名——「入侵」我们这间K记。
那个「亲信」,我依稀记得名叫Michael Holt,美国人,貌似棺材精。他其实是个监制(producer),却不知怎地变身成为了创作总监,还带了个华籍的美术总监过档。
我和这个棺材精,不知何解,无法相处。不知是他样衰还是态度问题,总之见到他我就无明火起。我们的「合作程度」,从以下的对话可现一斑:
棺:Richard,你可以为我把这段英文译为中文吗?
我:当然可以,如果你可以为我把这段中文译为英文。
棺:但我不懂中文。
我:那是你的问题。
厌倦森林
天天这样「斗争」,和「不合作」,我开始感到疲倦。
脾气越来越差,烟抽得越来越多。要不是我还可以以填词来平衡一下,我恐怕我早已疯了。我那首想回到平淡、不再指桑骂槐、不想追名逐利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好像也是在这期间写的。
每天,我都不想上班。即使回到公司,也是扳着脸。我还先后把两位女同事弄哭了,因为我不肯修改稿件,也不肯和客户开会,教她们无法向客户交代。她俩本来都是跟我谈得来的好同事。
许多时候,我在公司附近的茶餐厅吃早餐,吃至十一时许仍不离开。一边狂抽烟,一边填词,我根本不想见到公司那些鬼。拍档阿财,有时要走来找我,并「劝」我返工。
不过,即使返回公司,午膳时我又会吃到三四点,才再会在公司露面。
我实在很倦很倦,我不能继续这样过日子。我很想,很想离开这个广告界森林。
后记
后来发生的事情,有点复杂。
总之,机缘巧合,一九八八年,我脱离了广告界,加入了黎智英的集团。他改变了我的下半生。
最精彩的一句
苹果计算机创办人之一Steve Jobs,还是个廿来岁的嬉皮士时,欲邀请当时百事可乐的总裁(四十多岁)加盟,便对他说:「你打算下半世继续卖糖水(sugared water),还是你想改变世界?」
我不想下半生也卖糖水。
林振强
原刊于《壹周刊》
转自:Facebook
【作者简介】 林振强(1947-2003.11.17),绰号洋葱头、强伯、傻强,香港著名填词人兼专栏作家、漫画家、资深广告撰稿员、创作总监,是广告界出名的鬼才。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间,活跃于香港填词界,留下过千作品,与当时香港粤语流行曲著名填词人黄伟文、林夕、林振强并称“二林一黄”。 2003年11月17日凌晨林振强因淋巴癌病逝,终年56岁。
相关推荐换一批
- loading...
-

AKQA
-

上海宝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宝尊电商成立于2007年初,提供以品牌电子商务为核心的全链路一站式商业解决方案,涉及店站运营、数字营销、IT解决方案、仓储配送、客户服务等5大内容。 宝尊电商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和客户需求为引擎,致力成为全球品牌电商4I商业伙伴。
-

柠川文化
柠萌影业旗下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

华扬联众
华扬联众Hylink 是以驱动增长为核心、整合全渠道营销的信息技术服务公司
-

Interbrand
Interbrand是⼀家国际领先的综合性品牌战略顾问和设计公司,拥有管理咨询公司的严谨策略和分析技巧,同时也具备极富创意的品牌推⼴及设计优势。Interbrand为客户提供全⽅位的品牌咨询服务为他们创造和管理企业和产品的品牌价值。
-

FCB 博达大桥
-

前线网络 Front Networks